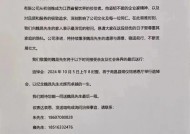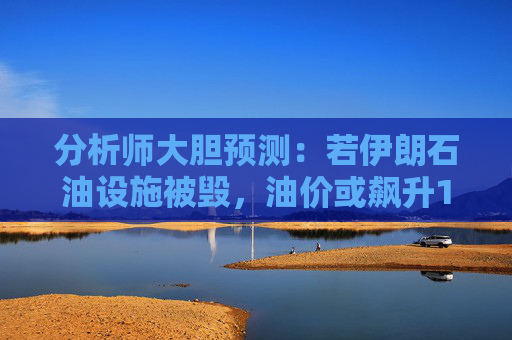裘劭恒与1946年涩谷事件
- 每日学习
- 2024-09-27 15:52:57
- 37
1946年7月19日,中国台湾籍华侨车队在日本东京涩谷警察署前遭遇日本警察袭击,造成台籍华侨6人死亡,21人受伤,43人被捕,冲突中日本警察1人死亡,3人受伤。这一事件在当时的媒体报道和后来的历史回顾中,一般被称为涩谷事件。事件发生后,中国舆论和中国政府认为华侨是受害者,要求严惩肇事警察。美国主导的盟军总部认为事件是台籍华侨寻衅滋事引发的,被捕的华侨破坏了占领秩序,应接受占领军法庭审判。中国驻日代表团无力改变盟军总部的立场,只好退而求其次,要求法庭中应该有中国法官。盟军总部同意涩谷案件由两名美国法官和一名中国法官一起审理。中国驻日代表团于是指派裘劭恒出任本案的中国法官。

裘劭恒
裘劭恒,1913年出生于江苏无锡,初中就读于上海东吴第二中学校,高中就读于上海沪江中学。1932年进入东吴大学法律学院学习,在学期间,考取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英语翻译,并在其兄长的律师事务所担任助理。1935年大学毕业后,先后担任东吴大学讲师、执业律师、公共租界工部局劳工课主任、中国银行人事课长等职。1946年初应邀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的秘书兼助理检察官。
涩谷案于1946年9月30日第一次开庭,同年12月10日宣判。判决结果是,在38名被起诉的华侨中,1人被判3年劳役,35人被判2年劳役,2人无罪释放。涩谷案件的判决结果,引起了国内舆论的强烈不满。《群众》杂志评论说,这次事件说明美国“不惜牺牲台胞的利益来助长日本法西斯的力量”。(《涩谷事件》,《群众》第十三卷第十期)
学界对于涩谷事件已经有不少研究,使用的材料各有侧重。杨子震《从帝国臣民到在日华侨——涩谷事件与战后初期台湾人在日本的法律地位》(《帝国臣民から在日華僑へ——渋谷事件と戦後初期在日台湾人の法的地位》)侧重日本方面的史料;Adam Cathcart的《战败国射出的子弹:1946年涩谷事件》(“Bullets from a Defeated Nation: The 1946 Shibuya Incident”, in Barak Kushner and Andrew Levidis, eds., Imperial Violence, State Destruction, and the Reordering of Modern East Asi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20)侧重利用美国国务院和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部的档案;卞修跃的《1946年东京涩谷事件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23年第1期)侧重使用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这些研究深入探讨了涩谷事件对于战后中美日关系、日本去帝国化和台湾去殖民化的影响。然而对于涩谷事件的过程,各方的研究仍未达成共识。对于涩谷案件判决的法律依据,也缺乏深入探讨。
裘劭恒法官在1946年12月10日涩谷案件宣判时,就当庭提出异议,并于第二天向对此案具有刑事管辖权的美国驻日第八军提交了书面的异议。这份书面异议在上述各项研究中均未被提及。笔者在1947年3月8日的《密勒氏评论报》上读到了这份文件(标题是“The Shibuya Case”),感觉这份从主审法官角度对案件的描述和分析,对于我们了解涩谷事件的整个过程极有帮助。下文即以这份书面异议为核心史料,结合前人的研究,再现涩谷事件的经过。
涩谷事件的背景
裘劭恒书面异议包含引言、控方证据、辩方证据、结论等四个部分。其引言明确了起诉人数和起诉理由:
这是一起针对43名被告提起的刑事诉讼,其中5名被告的诉讼请求已被撤回,剩下38名被告。
这些被告被指控犯有有损于占领目标的行为,特别是非法持有危险武器,错误和非法地协助、教唆和参与骚乱和争斗,使用斥责和挑衅性语言,以暴力和威胁的方式行事,开枪扰乱治安,导致数人死亡和其他人受伤;干扰日本警察合法履行职责,扰乱治安,恐吓附近居民。
这43人都是台籍华侨,他们的被捕与日本警察整顿黑市有关。二战期间,日本工厂招募了很多台湾工人。日本投降的时候,留在日本的台湾人有34,368人,他们陆续返回台湾,到1946年3月,还剩15,906人(杨子震)。这些台籍华侨很多都是在东京车站附近的黑市上摆摊为生。黑市是日本帮派组织的天下,日本警察在没有美国宪兵陪伴的情况下都不敢涉足。台籍华侨在新桥站黑市的摊位据说是向松田组浪人租借来的(卞修跃),实则摊位摆在车站广场上,而广场的所有权本来就不属于浪人。1946年3月开始,松田组开始向台籍华侨要求交还摊位,遭到拒绝后,双方屡起冲突(卞修跃)。关于双方冲突的另一种说法是,松田组向台籍华侨的摊位收取保护费,华侨不愿缴纳,导致冲突(尤伟仁:《日本“涩谷事件”亲历记》,《天津和平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7月中旬,日本警察开始整顿黑市,涩谷摊贩与警察发生冲突的报道时见报端。依赖黑市谋生的台籍华侨于是跟日本黑社会和日本警察都存在矛盾冲突。
涩谷案件在占领军法庭审判,由美国检察官起诉。这里关系到司法管辖权的问题。根据盟军总部1946 年 2 月 19 日发布的《总司令部关于刑事审判管辖的备忘录》,驻日美军第八军司令官和第五舰队司令官对损害占领军安全或利益或违背占领目标的行为拥有管辖权,并规定设立“占领军法庭”作为行使管辖权的机关。因此,裘劭恒在引言中介绍的起诉理由中,最重要的指控就是被告犯有“有损于占领目标的行为”,因为这项指控确定了本案的管辖权属于驻日美军第八军司令官及其设立的占领军法庭。
肇事者还是受害者?
涩谷事件争议的焦点,在于确定台籍华侨是肇事者还是受害者。美国军方的检察官认定华侨是此次事件的肇事者,根据裘劭恒的概括,控方对于事件的叙述是这样的:
1946年7月19日之前,台湾人与涩谷警察和其他日本人发生了多起事件。警方接到报告称,台湾人将袭击松田组,松田组是一群臭名昭著的日本人,曾多次与台湾人、警视厅和涩谷警察署发生冲突。为了以防万一,涩谷警察署得到了邻近警察署的增援,并设置了路障检查驶往警察署的车辆。7月19日晚9点左右,一支由中国驻日代表团吉普车护送的载有台湾人的卡车车队在驶向涩谷警署时被警察截停。吉普车上的乘客告诉警察署长,这些台湾人是在中国驻日代表团开会后回家的,警察署长允许车队通过,并在吉普车上安排了一名警察以确保车队通过。
与此同时,卡车上的人大喊大叫、辱骂、挥舞棍棒、吐痰,其中两人还被看到用手枪指着警察。当车队继续行进时,第三辆卡车开了三枪,一名警察被击中。警察开枪还击,双方交火持续了一小段时间。另一辆吉普车和又一辆卡车驶近,后者的乘客大声喊叫并开枪,警察开枪击中了司机。卡车与对面的房屋相撞。车上的人被逮捕,没有发现他们持有枪支,但后来搜查时在卡车内和附近发现了武器和弹药。
裘劭恒又转述辩方叙事如下:
1946年7月19日下午,400-500 名中国人(大部分是台湾人)聚集在昭和小学,讨论7月16日松田组流氓的武装袭击事件。中国驻日代表团侨务处处长林定平先生在会上发言,表示中国驻日代表团将对事件进行调查。会议结束,与会者离去,一名中国人在回家的路上遭到日本流氓的侮辱和威胁。他回到学校后,仍在学校的人决定向中国代表团发出呼吁。
他们来到中国代表团,中国代表团顾问李立柏将军向他们发表了讲话。他的讲话内容与林先生的相同。在举手表决对演讲表示满意后,台湾人散去。为了避免松田组可能发动的袭击,台湾人要求并获得了中国驻日代表团吉普车的护送。
六辆卡车分三支车队出发,每个车队由一辆吉普车护送。一支车队顺利开往新川。另一支由一辆吉普车、一辆轿车和两辆卡车组成的车队在涩谷警察署附近被日本警察拦截。在吉普车乘客作出解释并获准继续前行后,道路两侧突然传来一阵枪声,警察将枪口对准了卡车。吉普车和车队逃往中国代表团。
第三支车队在接近警察署时遭到无端射击;一名卡车司机受伤,他的车撞上了路对面的一栋房子,车上的人被逮捕。事件中有6名台湾人死亡,21人受伤。
这两种叙事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控方认为台籍华侨在卡车上大喊大叫、挥舞棍棒、谩骂、吐痰,在第三辆卡车上开了三枪并击中一名警察,在第四辆卡车上开枪。而辩方认为,华侨没有开枪,枪声是从街道两边响起的。而最后到达的卡车(即控方所谓第四辆卡车),更是刚接近警署即遭射击,全体乘客被无端逮捕。
根据后来的研究,涩谷事件发生的当晚,埋伏在涩谷警察署附近的警察有将近四百人(Adam Cathcart)。控方所提交的证物中包括三支手枪。即使这三支手枪真的是台籍华侨携带的,也很难想象他们会凭借这些武器去主动攻击这么多警察。从他们要求中国驻日代表团吉普车护送回家的举动来看,也不是去寻求冲突的。在整个事件中,大约90名警察开枪射击(Adam Cathcart),击发子弹超过250颗(杨子震)。可以说,这是日本警察对于台籍华侨的一场单方面的屠杀。除了这些警察之外,松田组黑社会也准备伏击华侨的这些卡车,他们提前组装了一挺机枪,当听到卡车接近的消息后,即有人带着机枪爬上附近学校的屋顶,并击发了一组子弹。不过警察很快逮捕了机枪手(Adam Cathcart)。
华侨在战争结束后萌生了一种战胜国国民的自豪感,即使面对日本黑社会,也不愿意轻易屈服,因此与松田组发生了一些小范围的冲突。涩谷事件的发生,实际上是日本警察和日本黑社会对于台籍华侨展开的一场联合打压。这次打压还受到了美国占领军的支持,因为这些连黑道规矩都不服的华侨,损害了美国的占领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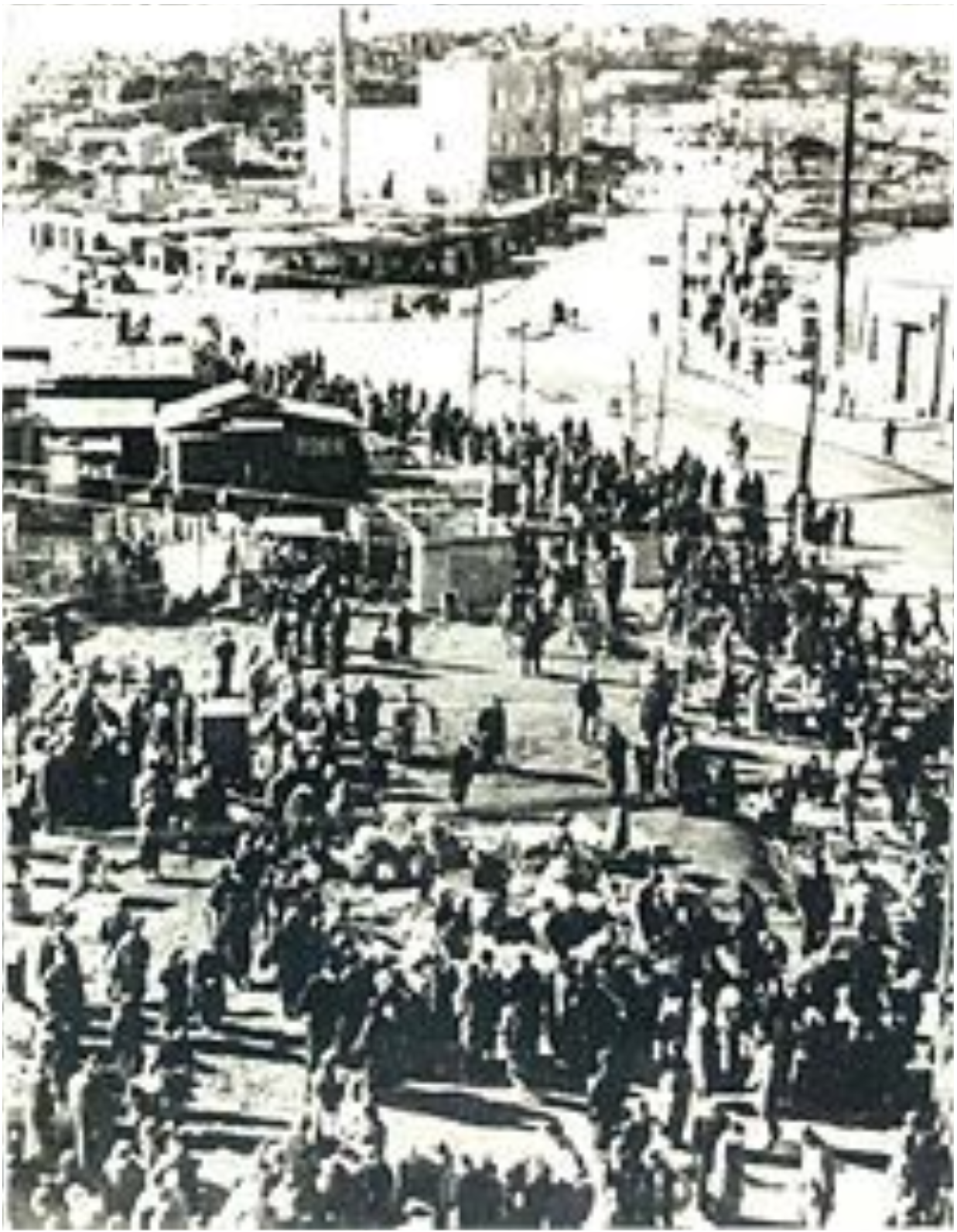
1945年的东京涩谷
没有证据的判决
裘劭恒在书面异议中明确指出占领军法庭对于涩谷案的判决是缺乏法律依据的。他首先指出,被告之间并不存在共谋行为:
所提供的证据均不利于共谋的存在。在事件发生前的会议上,警方没有被提及;台湾人对李将军承诺的代表团行动表示满意。再者说,出席会议的大部分台湾人都顺利返回了家中,这表明并没有有计划的袭击。此外,中国驻日代表团吉普车的驾驶员在没有台湾人授意的情况下,选择了三条路线中最短的一条,即路过警察署的那条。卡车被拦下后没有直接发生战斗这一事实说明没有预谋。
为了说明华侨并没有进行袭击警察署的共谋,裘劭恒提出了上引5条证据。其中第一条证据中所说的“警方没有被提及”,回避了华侨集会中讨论过如何对付松田组的问题,也就是说,华侨们或许有意与松田组对抗(尤伟仁),却无意于对抗警察。第二条所谓“李将军承诺的代表团行动”,指的是中国驻日代表团承诺将对7月16日松田组袭击华侨摊贩一事展开调查。在排除了共谋的可能性之后,裘劭恒进一步指出控方对于每一名被告的罪行负有分别举证的责任:
在没有任何关于共谋的指控或证据的情况下,必须有明确的证据将每名被告与他被指控的特定罪行联系起来,控方有“举证责任”证明被告有罪,排除合理怀疑。控方关于被告是否有罪的唯一争论点是,被告在事件发生时仅仅出现在该地区,而且他们没有下车离开,以摆脱任何参与和责任。然而,在警察署长允许他们通行时,台湾人没有理由预料到会有麻烦。此外,他们获准通过这一事实也表明,他们所谓的扰乱治安行为并没有达到需要警察干涉的程度。当然,第二车队的卡车乘客没有机会下车脱离。因此,我不同意仅凭被告在场且未下车就可以在法律上确定被告有罪的说法。
没有证据表明任何一名被告开枪或以其他方式参与扰乱治安。即使那一位承认持有手枪的被告也没有开枪的证据。关于哪方首先开枪的证据自相矛盾,唯一的无利害关系证人,一名美国平民,作证说他没有看到卡车上的人开枪或骚动。
本案传唤了六十多位证人,大部分是具有利害关系的日本警察(卞修跃)。但是除了一位被告承认非法持有枪支以外,这么多的日本警察都无法指认其他任何一位被告犯有哪项特殊的罪行。检察官最后只能凭借被告“在场且未下车”作为犯罪证据,这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关于警察和华侨谁先开枪的问题,亲历者高玉树后来回忆说有可能是卡车上的人先开的枪(杨子震)。但是在法庭上连任何一个华侨开过枪都不能证明,更不用说是否先开枪的问题了。
于是,裘劭恒作出了最后的总结:
最后,我想重申,证据必须在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表明,每名被告犯有指控书中所列的一项或多项罪行。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中既没有指控也没有认定共谋。因此,必须有明确的证据将每名被告与指控中的罪行联系起来。然而,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任何一名被告有罪,只有第21号被告例外,他承认在事件发生时他持有一把手枪,尽管证据显示他在事件发生的任何时候都没有开枪。
鉴于上述理由,我不同意委员会的裁决,我认为,对所有被告都应作出“无罪”判决,但第21号被告除外,他只应因非法持有危险武器的第1项指控而被判有罪。
裘劭恒的结论是非常具有说服力的。这些华侨之所以被捕,不是因为他们袭击了警察,而仅仅因为他们的卡车被警察袭击之后无法逃离。
中国国民政府和驻日代表团在涩谷事件发生后与盟军总部展开交涉。8月31日,驻日代表团根据外交部指示向盟军总部提出了涉事警察革职、日本政府道歉、伤亡赔偿等十项要求,试图通过政治途径解决此案。在美方决定将本案作为治安案件处理时,国民政府对于案件的胜诉完全没有信心,也不作努力,转而把交涉的重点放在要求对等地起诉涉事日本警察上。外交部亚东司司长杨云竹认为:“我方有利证据太少,台侨可指责之处太多。藉此案交涉,甚或与总部对抗,似难成功,亦不相宜……我所能作者,目前在要求拘捕犯案日警,进行审讯”(转引自卞修跃)。这种交涉思路把重点不是放在维护本国国民的合法权益上,而仅仅放在惩罚对方警察上面,无疑是对外交资源的浪费。且在默认华侨将被判有罪的前提下,如何能指望惩罚涉事警察?在涩谷案宣判后,占领军法庭又象征性地起诉了三名日本警察,不久即宣告无罪释放。
年轻的裘劭恒法官在占领军法庭上孤立无援,只能通过书面异议来寻求公正、保留真相。从他提供的证据来看,36名被判刑的台籍华侨中,只有一名被告可以因非法持有危险武器而获罪,其他人都是无罪的。国民政府的无效交涉仅仅是导致这些被告被冤枉的次要原因,而主要原因一在于日本警察屠杀在前构陷在后,二在于驻日美军为了维护所谓的占领秩序,不惜牺牲华侨的利益,对日本警察进行了没有底线的袒护。1946年涩谷事件的发生及其处理结果表明,在美军占领日本的前提下,与太平洋战争时期相比,中美和美日之间的亲疏关系已经发生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