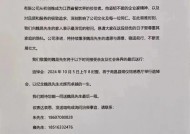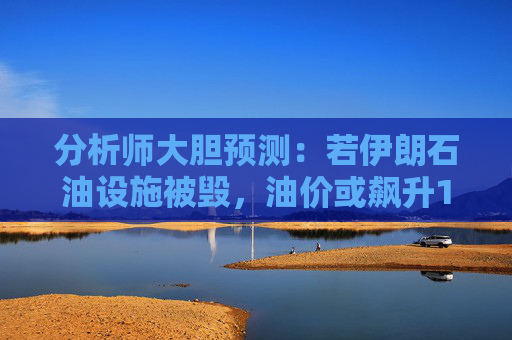陈正国:思想史的学术意涵
- 每日学习
- 2024-09-24 11:22:47
- 26
尽管中国传统历史载记中有精彩的思想史内容,但今日我们谈论思想史的时候,完全是从现代历史学学科的背景来理解的。这意思是说,思想史是历史学大家族的一支,她与其他分支共享了历史学的基本信念——求真。但对于什么是重要的历史事实,如何求真,如何解释重要的历史事件与现象,不同分科则有不同的定见。往坏处说,不同分科会形成陌路甚至党同伐异的现象;往好处想,不同的分科分别呈现了庐山——历史——的不同面貌与面向,历史也因此才真正成为立体图像。
既然思想史是现代历史学发展中的一支分流,中国思想史也必然会随着现代历史学的建构与发展而与世界历史学发生极为复杂的互动,包括挑战、回应、模仿、拒斥、自我本质化、他者化、伪造、创造性转换化等等各种做法。一百年前在争论全盘西化或部分西化的时候,胡适曾说,在态度上中国需要拥抱全盘西化,但无须担心中国会成为西方,因为所有的外来文化因子一定会受到传统文化的抵抗、限制、融合,所以所谓全盘西化其实不会出现。胡适当然非常向往西方民主制度、物质发展与科学态度,但他在什么意义上是全盘西化论者,不是本书所能论断。胡适显然有个朴素的见解,认为矫枉就是要过正才能得其中,因为固有文化或传统都会有惰性,会中和或减缓新加入因子的效力。但胡适没讲清楚的是:一个偌大社会中不同部门与人员“竭力”吸收外来文化之时,一定会受到现实环境的影响而自主或不自主地考虑如何使用、修正、选择外来因子。个别行动者所认知或接触的外来因子既不可能相同,其使用、改造的方式、程度也不会同步。换言之,在空间与时间错落不齐的环境中,外来文化因子一定会随着总体经验的累积而缓慢演化成在地社会所能接受的融合模态。用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的话来说就是,新世界观的理解与掌握,一定受旧世界观的限制与影响,两者一定会产生新的视域融合,不再是旧,也非全盘的新。用实证主义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必须相信每个人对于新观念、新事物的引进都会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尝试与修正,在一定的时间之后,我们才能看到整体的变化与新面貌。佛教传入中国成为“中国的佛教”,就是很具体而明显的例子(其实所有外来文化经过中文化就必然会形成在地化特色,尽管未必是人们心中理想的新样态)。可惜的是,青年胡适所处的中国在许许多多层面上都有激烈化的倾向,连温和的、倡议“改良”而非革命的胡适也难免掉入激情的文字游戏(障),欲以“全盘西化”而不是单纯的“西化”来宣扬自己的现代化态度。话虽如此,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在地演化与胡适对于新旧文化融合的想象应该是若合符节的。思想史作为一门学院专业,当然是从西方现代史学发展而来,但从一开始,其实践就与传统学术发生了正面的化学变化,其结果既开创出新的学术类型,又展现中国特色或在地特质。中国思想史的历史,绝对值得有识者投入研究,但本书无法对此做出任何详细的论述。相反地,此处讨论重点完全偏重在西方,尤其是英语世界的发展。
西欧在过去一百年,曾出现多种名称用来指涉关于观念、价值与世界态度的历史研究,包括英语的history of thought、history of ideas、intellectual history、the conceptual history,德文的Geistgeschichite、Begriffsgeschichite、Idees geschichite,法文的l’histoire des idees、l’histoire intellectuelle,意大利文的stori filosoph、 stori della idee,等等。法国历史学者侯杰·夏蒂埃说,如何叩问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是世上最困难的事,其中最主要的理由是相关专业术语在各国之中多有不同,彼此难以调适移译。中文世界读者对夏蒂埃的感慨应该很有共鸣,因为中文学界在使用“思想史”一词时,有可能代表上述任何一种学术或书写类型。中文世界使用“思想史”一词所表现出的宽泛倾向,比较接近英文的history of thought(法文histoire de la pensèe,德文Geschichte des Denkens)。在英语世界,history of thought是history of ideas以及intellectual history出现之前常见的选择。例如著名史家Leslie Stephen(1832—1904)在19世纪晚期出版了两册的History of the English Though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881)。History of thought这类书名在近期的英、法、德文出版界依旧时有所闻,内容比较像是“研究人类创造性思考及其产物”的一种统称,尤其是当该作品同时包括形上学、学术发展、科学理论、政治原则、美学、社会学等等内容的时候更是如此。或许可以这么说,History of thought相当现今中文学界对于“思想史”的广义用法。
思考或思想(thought)除了总括各种主题的心智活动与成果之外,也常用来表达某单一学科或主题的心智层面的探索与成果。最常见的名称有政治思想史(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与经济思想史(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在学院分科中,它们是政治学与经济学的次学科。尔来有环境思想史(history of ecological thought, l histoire de la pensée écologique)的倡议,自然是拜近几十年环境史蓬勃发展结果之所赐。自从1960年代迪维二世创造“历史环境学”(Historical Ecology)概念以来,环境史就稳定发展,吸引学者投入相关研究。经过三四十年的耕耘,学者也注意到人与环境、自然的互动,反映了人的观念与价值。中文世界除了起步最早的学术思想史写作,也陆续有“军事思想史”“文学思想史”“制度思想史”与“地理思想史”等研究类型的加入与提议。从理想上讲,这类科别或主题式的思想研究,目的是在补充原有科别或主题的不足,尤其是涉及“价值”或“意识形态”的研究。表面上看,某一学科越宣称具有自然科学般的客观性,就越会对其学科的思想史抱持可有可无的态度。对物理学家或逻辑哲学家来讲,“物理思想史”或“逻辑思想史”这些概念是自相矛盾的名词。物理学本身就是人类思考物理世界的充足内容;物理学之外,再无思想。尽管现代科学哲学开始反省,认为物理学者的主观想望会影响他们的研究结果,但这样的意见短期内很难成为物理学者进行实验或研究时的反思性前提。现代经济学普遍预设“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两种经济认知类型,“规范”涉及价值或“应然”的取舍,而“实证”则是要建立足以解释“实然”的模型与科学。行政部门、政治领导人会考量施政后果而做出规范,例如给特定产业优惠、为特定族群免税,但是硬核的经济学只考虑经济现象(包括政府政策因素)的实然。
相对于宣称科学性质浓厚的学科,有些学科本身就是沿着价值的叙述、情思的表露而发展,其学科的思想史就占据相当核心的地位,例如文学。相对号称不需要思想史的物理学,一部文学史若没有思想或观念分析,那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事。依此而言,环境事关人类的生存、健康、幸福、经济、发展甚至国家强盛等等价值,环境思想史必然会逐渐为人所重视,大概是预料之中。中国制度思想史的出现让研究者得以重新体会、揣想古代设定各种制度在人心中的价值、目的或理想,这类似于钱穆在谈中国政治制度时喜欢讲的制度背后的“精神”(类似民族或集体智慧。钱穆喜欢引孟子的“所过者化,所存者神”,这个“神”应该就是他讲的历史精神)。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发现,思想史研究有个作用,就是透过追问我们习见的历史解释背后更深远或深刻的动机、目的、价值取向,而得到单从制度或现象表面得不到的历史理解或感悟。当然,很多历史上的行为,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都未能留下行为者的自述。所以欲理解其动机与目的,常苦无直接证据而需要运用间接证据以及字里行间的讯息、解码等来铺陈,有时难免会有故作解人、过度诠释的问题。甚至有时候会假设历史本身自有一种理性,不然一种制度不会存在三五百年,甚至上千年。只是这种制度或历史的理性,常常是作者将自己摆在后观者,或俯视者的视角所建构出来的历史想象与解释,例如黑格尔会说近代欧洲的历史精神就是自由。
相对于代表泛称与专科次领域的“思想史”,目前学界讨论最多的思想史课题,是相对应英语的history of ideas以及intellectual history。这两种文类是自足的或自成规矩、规范的思想史,而不是其他学科(如政治史或经济史)的次领域。自有规范的思想史是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海洋史、科学史、医疗史、制度史、宗教史、环境史、军事史、文化史、艺术史这样的史学次领域并列的学术科别。这意思是说,人们相信人类的价值、意识形态、信仰、情感、道德原则等等关乎心灵与心智活动的现象与成果的本身,值得仔细追问与研究,值得用特别的研究方式与书写方式来呈现;研究历史上重要的心灵与心智活动,以及这些活动的结果和影响,与研究重要的战争、宗教、经济、政治制度同等重要。如果我们说,人之所以为人,正在于人会依据价值系统、意识形态、道德原则之不同而建立不同的社会与群体,那么研究这些价值、意识形态、信仰、情感、道德原则就成为研究人类与人类社会的第一要务。极端一点说,所有的历史都是人类有意识的行动之后的结果。思想史就是研究这些意识的内容,以及它们为何出现在特定的时空,它们与其他历史力量如何互动、影响。

(本文摘自陈正国著《什么是思想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6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