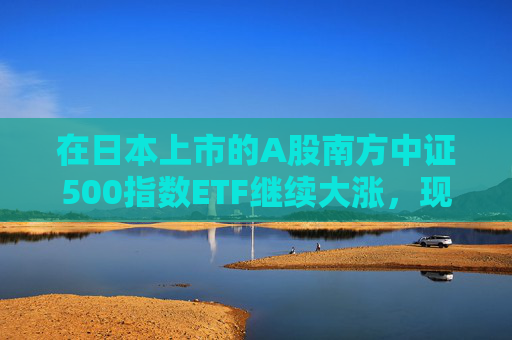陈丹燕:浦东美术馆的永久收藏品
- 每日品味
- 2024-09-23 15:54:46
- 20
浦东美术馆将陆家嘴框为美术馆永久收藏的作品。

许多年前,还是东方明珠时代,汇丰银行要回上海,正在陆家嘴造新大楼。我刚刚在准备写《外滩三部曲》,曾跟一位本地的纪录片导演讨论过陆家嘴的崛起。他说,陆家嘴是外滩的儿子,没有外滩就没有陆家嘴。这是我受到的黄浦江两岸关系最初的启发。
日后,在浦东美术馆镜厅,整条外滩如一幅大画那样展现在所有参观者面前时,他的那句话又回到我心中。这是一个开阔而平视的角度,完美。有时我黄昏时分去,看得到落日从外滩背面庄严地燃烧着落下,江水熔金,从杨浦滨江那边开来的黑船缓缓犁开耀金的江水,好像灿烂的欢笑。有时我初冬时分去,南北交汇的冷暖气流在江上交汇成灰白色的雾,外滩的大楼就在雾里隐现,好像往事萦绕时的老人的眼神。建筑师说这是浦东美术馆著名的“第四维空间”,是展示城市艺术的一个恒久的作品。对我这个作家来说,这里让我感受到一个长大成人的儿子对父亲的注视,他沉稳地与父亲隔江对坐,是因为他来路分明,心思安顿。所以在镜厅里,不论看到怎样的外滩,它都会令人生起敬意,在心里喟叹一声。

镜厅还有一个好处,是能看到镜像里的外滩。想要看到镜像里的外滩,你必须进入到镜子面前,因此你不得不看到自己,打量一下你自己跟外滩的关系。这是在上海看外滩最佳的视角,对上海人来说,也是看自己和外滩关系的最警醒之处。
如果套用曹景行问题的句式:外滩与你本人是什么关系?或者说,你与上海是什么关系?
我写《外滩三部曲》时,时时问自己这个问题。一个人把自己写作生涯中精力最充沛的十年花在对外滩的田野调查和写作上,到底有什么必要?
在镜厅我望着对岸的那些房子,那十年里我一直在这些建筑里出入,拍照片,坐在冰凉的大理石或者水磨石楼梯上,努力感受老建筑内里聚集的时光,或者进入多年空关的大楼房间,为身体搅动了无数螨虫而戴好口罩免得打喷嚏。在江对岸看着它们不论阴晴总是阴沉的样子,亲切又陌生的感受,这就是一个人对自己所在的巨大城市的感受吗?有时我想,不知道一个伦敦人在泰晤士河的格林威治岸边会有我这样的感受吗?本来在2020年,我会作为中国作家去参加伦敦国际书展,已经在计划书展结束后,我将要去参观泰晤士河畔的码头博物馆,去见识一下泰晤士河对伦敦人的影响力;也会去找一下那里是不是还保留着海事时代码头工人号子的资料。听汉堡海事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世界上的码头工人搬运号子都是一样的节奏,因为人类步伐都是一致的。但是2020年我所有的洲际旅行都取消了,伦敦书展也停办了。

在这个镜厅里,眺望外滩,总是想到全世界相似的通商口岸城市,因为它们都有相似的面容吧。
不过,也许只有浦东美术馆,用一个镜厅来致敬它特有的面容,将它框为美术馆永久收藏的作品。外滩因此也率先成为了永不可移动的城市面貌。